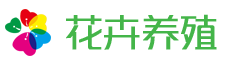现代文学以来,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比老舍更熟悉北京、更热爱北京文化,更能够代表北京普通市民的道德情感结构与观察世界的眼光与态度。作为一个出生于北京并且深受北京文化影响的北京旗人后裔,老舍尽管在后来几度出游海外,漂泊川鲁,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,一生67年中在北京度过42年。
无论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叙事背景、环境乃至叙事主角,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的文化中心、文学市场乃至意识形态想象的根源,北京无疑都是老舍创作的起点和归宿。可以说老舍的创作有着难以割舍的 “北京情结”,“生在北京,长在北京,死在北京,他写了一辈子北京,老舍和北京分不开,没有北京,就没有老舍。”

老舍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但自幼家境贫寒,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的一所大杂院中,前半生又在各地漂泊,在北京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宅院,解放前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共有九处,直至解放后才自己出资购买了一所四合院作为住所,并在此居住直至辞世,现被辟为老舍纪念馆。

丰富胡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,老舍故居位于西侧,院东侧辟一座砖砌门楼,入门可见一座砖影壁。门南侧有三间倒座房,由看门的工友居住。砖影壁西面是个小跨院,内设平屋顶正房两间,为家中男孩卧室,白天兼作老舍私人秘书南仁芷办公室,对面的两间小房分别用作厕所和贮藏室。

从前院通过一个中门可进入正院。正院较为宽敞,北为正房三间,两侧各设一间耳房,东西设厢房各三间。正房的明间和西次间用作客厅,东次间为老舍夫人胡絜青的画室兼卧室,东耳房是卫生间,装有抽水马桶和洗澡盆。东耳房的墙外还有一间小锅炉房,里面装了一台小暖炉,供冬季全院采暖之用。

西耳房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,其中设有特制的大木床和大壁柜。老舍先生在此居住的16年中创作了24部戏剧剧本和两部长篇小说,其中以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和未完成的《正红旗下》最为著名。东厢房最北一间为厨房,南二间为餐厅,西厢房三间用作女儿卧室。

这个院落很整齐,保存着一个大铜缸。1954年春天,老舍先生在小院中亲自栽下了两棵柿树。每逢深秋时节,柿树缀满红柿,别有一番诗情画意,为此胡絜青美其名为“丹柿小院”,并将画室称为“双柿斋”。

老 舍的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,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。 襁褓之中家曾遭八国联军劫掠,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。 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。 1913年,考入京师第三中学(现北京三中),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,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, 于1918年毕业。

老舍的一生,总是在忘我地工作,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“劳动模范”。他自己说:“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,发表也好,不发表也好,我要天天摸一摸笔。”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(尤其是长篇小说)、剧本、散文、诗歌(新式之外包括歌词、古词和旧体诗等),几乎什么形式都涉及了。已经出版的《老舍文集》19卷,总共有一千万字之多,包括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《茶馆》《二马》《月牙儿》《断魂枪》等大量文学作品,创作的《龙须沟》赢得了“人民艺术家”的崇高赞誉,受到人们的喜爱。他的短文、散文《养花》《猫》《济南的冬天》《茶馆》《草原》《想北平》和《我的母亲》相继被收录在中小学生课本里。

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,另有絜青、絜予等笔名。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,父母为他取名“庆春”,大概含有庆贺春来、前景美好之意。上学后,自己更名为舒舍予,“舍予”是“舒”字的分拆:舍,舍弃;予,我。含有“舍弃自我”,亦即“忘我”的意思。这个“老”并不表示年龄大,而是含有一贯、永远的意思,合起来就是一贯、永远“忘我”。他用“老舍”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,以致不少人只知道 “老舍”而不知舒庆春是谁。

1961年至1962年,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《正红旗下》。遗憾的是未完成,就被迫停笔。文革中,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,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。1966年,他被逼无奈,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,享年67岁。